
麻雀該劇根據編劇海飛的原著小說改編而成,主要講述了陳深潛伏在汪偽特工總部首領畢忠良身邊,通過代號為“麻雀”委派的工作者秘密傳遞信息,成功“竊取”汪偽政府“歸零”計劃的故事,《麻雀》最新劇情講述的是什么,麻雀最新劇情介紹至大結局。
《麻雀》原著小說麻雀第35節劇情
第23章
那天晚上蘇響是一個人回家的,陳淮安不能把她送回去。蘇響牽掛著家里的盧揚和程三思,她轉過身把背影留給了米高梅舞廳的那些紅男綠女,一步一步從容地向舞場門口走去。當她站在米高梅舞廳門口的時候,才發現這是一個細雨中的夜上海,所有的燈光因為雨而顯得朦朧。一輛黃包車像是在水中滑行的泥鰍一樣出現在她的面前,她上了黃包車說,去西愛咸斯路73號。
車夫身上的車衣已經被微雨打濕了,他的頭上戴著一頂氈帽,寬闊如門板的身板在跑動的時候不停地搖擺著。當黃包車在公寓樓下停穩的時候,蘇響淡淡地說,你怎么當車夫了?
陶大春摘下了頭上的氈帽回過頭來笑笑說,還是被你認出來了。
蘇響說,我問你怎么當車夫了?
陶大春說,我不在貨場做了。
蘇響不愿再問,她把一小卷潮濕的錢塞進陶大春的手里,然后走進公寓樓的門洞。陶大春拿著錢,一直愣愣地看著一個旗袍女人走進一片黑暗中。看上去蘇響就像是被一堵墻吸進去似的,這讓陶大春想起了《聊齋》。
在三樓朝北房間慘淡的燈光下,蘇響用干毛巾擦著頭發。盧揚和程三思顯然已經睡著了,來照看他們的梅娘坐在床沿摳腳丫吸煙,屋子里已經布滿了煙霧,地上有一只“小金鼠”的煙殼。蘇響一邊擦著頭發一邊不耐煩地說,少抽幾支你會死啊?
梅娘笑了,不用你管。
蘇響懶得再說她,她看不慣梅娘的做派。梅娘十分清楚蘇響的心里在想什么,她竟然沒有回六大埭的住處,而是找了一床薄被拋在沙發上,然后無賴般地躺了下來。
梅娘說,今天晚上我住這兒了。我想和你談談工作。
梅娘沒有談工作。梅娘在談她自己的事,她對自己的事有十分濃厚的傾訴欲,她說她當大小姐的辰光,在老家諸暨的筆峰書院里讀書,家里有多得不得了的山地和竹林。她對自己家族的敗落耿耿于懷,她姓斯,她的祖上曾經因為救過一個強盜,而強盜的報恩讓她們家發達了,如此種種。
我們家一定是書香門弟。梅娘斷然地說。
蘇響對這些都不感興趣,躺在床上她一手攬著盧揚一手攬著程三思,心里想著遙遠的江西,在叢林里奔突與沖鋒的程大棟。蘇響想,大棟現在一定是一個強壯的、黝黑的、胡子拉碴的人了。在這樣的念想中蘇響沉沉地睡了過去,睡過去以前她聽到梅娘的最后一句話說,我和你一樣,身邊沒有男人哪。
這時候蘇響就在心底里輕笑了一下,我那不是沒有男人。為了勝利,我男人在叢林里。
陳淮安是在上海進入初秋的時候向蘇響求婚的。秋天的風經過了沙遜大廈的樓頂露臺,陳淮安的頭發被風吹起,他把目光從遙遠的上海天空中鉛灰色的云層中收回來,突然對蘇響說,你嫁給我!
蘇響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陳淮安接著說,我是認真的。
蘇響仍然沒有說話。陳淮安說,你必須表個態。
一直到黃昏來臨,蘇響還是沒有表態,她只是微笑著任由秋風把她的頭發吹來吹去。那天晚上陳淮安請蘇響在沙遜大廈8層的中式餐廳一起吃飯。陳淮安的興致很高,他喝了至少有一斤紹興酒。一直到晚餐結束,蘇響仍然沒有給他答復。她只是這樣說,你對很多人說過同樣的話吧。這讓陳淮安十分掃興,他盯著蘇響看了大約有三分鐘,長長地嘆了口氣說,你是一個奇怪的人。蘇響順著陳淮安的話說,我真的是一個奇怪的人。第二天蘇響就在梅廬書場的一個小包廂里把這件事告訴了梅娘,蘇響說算我向組織上匯報吧。梅娘點了一支煙站起來來回踱步說,你當然應該匯報。蘇響說,那我該怎么辦?梅娘笑了,從現在開始你是單身,沒有人知道你是嫁過人的老黃瓜。蘇響皺起了眉頭,你說話真難聽。梅娘說,真話一向難聽。你必須接近陳淮安。蘇響說,這是組織上的意思,還是你的意思?梅娘說,組織上我會匯報。一會兒,梅娘又加了一句,但這更是我個人的意思。蘇響說,那你就給我閉嘴。我有盧加南,我是有男人的,我不像你!梅娘一下子就愣了,她的臉上迅速地掠過痛苦的神色。像是胃病發作似的,她緊緊地捂住了胃部。看上去她明顯地軟了下來。她說那這件事你再考慮一下。另外組織上要啟動3人新電臺,組建 5號交通站,你是報務員,我是組長。譯電由我負責。
梅娘十分倉促地說完這些話后,就把自己的身體卷成一團,緊按胃部坐進一把椅子里。
那天蘇響破天荒問梅娘要了一支煙,梅娘用火機為蘇響點著了煙。在劇烈的咳嗽中,蘇響把一支煙抽完,然后她重重地在桌子上撳滅了煙蒂說,孩子怎么辦?
梅娘臘黃著一張臉說,孩子我來帶,你可以寬心。要知道我是書香門弟出身,知道怎么教孩子。
蘇響覺得自己一下子變得無話可說了,那是在和無趣的人,把該說的話都說完了以后才會有的反應。她順手拿過了一張《大美晚報》,目光在那些黑黝黝的文字上凌亂移動時,發現一張形跡模糊的被抓拍的照片。照片上一個熟悉的背影,顯得十分得遠而小。他正在打開車門鉆進汽車。而不遠處是亂哄哄的人群,一個穿西服的男人仰天倒在地上。他的頭部有血滲出,在報紙上像一塊被不小心沾上去的墨汁。
蘇響知道,這是國民黨軍統戴老板派出的人在上海灘上鋤奸,在此前的幾年里,已經有許多漢奸倒在了血泊中。蘇響還知道,這就是所謂的因果,當漢奸是總有一天要還的。
蘇響小心翼翼地把那張報紙收了起來。那天她離開梅廬的時候沒有和她告別,而是匆忙地離開了那間包廂。后來她終于明白,她連一句話也懶得和梅娘多說。
一個月后的清晨,陶大春在西愛咸斯路73號公寓樓樓下不遠處的小弄堂里截住蘇響。那天的天氣已經有些涼了,蘇響穿著厚重的秋衣去菜場里買菜。陶大春對蘇響笑了,蘇響也笑了,蘇響看到陶大春嘴里呵出了白色的氣霧,蘇響說你什么時候開始當殺手的。
陶大春的臉色變了,說你開什么玩笑。
蘇響把一張疊得方方正正的報紙掏出來,平舉到陶大春的面前說,這個背影就是化成灰我也能認出來。陶大春沉默不語,最后把那張報紙小心地裝進了自己的口袋。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說,我隨時準備死。
蘇響說,為什么準備死。
陶大春咬著牙說,為了勝利。
蘇響聽到了“勝利”兩個字,這讓她想起當初梅娘和她說過的話。梅娘讓她還給她兩個字:勝利!
陶大春說,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告訴你。你還記得那個厚嘴唇的阿六嗎?你在梅廬書場碰到過的那個小伙子。他才十九歲,可他已經死了。他媽生了六個兒子,現在一個也不剩了。
陶大春在這個秋天的清晨顯得十分激動。他只是想來看看蘇響的,他一點也沒有想到蘇響已經知道了他是軍統的人。他索性能順水推舟要蘇響加入軍統,并且告訴蘇響,他一定會做通軍統上海站站長的工作,給蘇響一個比較好的崗位。陶大春突然想到了陳淮安,他認為站長一定會希望和大律師陳淮安搭上線,那樣可以在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營救更多的軍統人員。陶大春越想越覺得動員蘇響加入到自己的陣營是對的,他開始喋喋不休地說動蘇響,但是蘇響卻十分平靜地說,我只想過小日腳。
陶大春說,那你還有沒有一個中國人的良知?
蘇響說,請不要再說這些。你走!
陶大春走了。他走路的樣子有些異樣,一條腿軟綿綿地拖著,顯然是一條壞掉了的腿。蘇響有些心痛,這個曾經心儀過的男人大概是受了槍傷。蘇響說,怎么回事?
陶大春扭轉頭來說,沒什么。你知道的,那天我們截殺漢奸馮銘博,我中槍了。就是報上登的那一次。
《麻雀》原著小說麻雀第36節劇情
第24章
陶大春認為他解釋得十分清楚了,所以他又轉過頭去,拖著一條病腿麻利地向前走去。蘇響一直望著他落寞的背影,她記起少年辰光陶大春的臉永遠是黃的,眼睛下有兩個浮腫如蠶繭的眼袋,臉上全是蛔蟲斑。那時候陶大春多么單薄與瘦小啊,在秋天的風里簡直像一張紙片。而現在他留給蘇響的背影,幾乎是一面移動的墻——魁偉,結實。
那次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沙遜大廈頂樓高大的金字塔房舉行的年度答謝招待酒會上,陳淮安喝多了。蘇響就坐在大玻璃窗邊,她喜歡吃螃蟹,所以她就用心地剝著層層蟹黃的螃蟹。她十分喜歡坐在窗邊看窗外的夜景。那天的斜雨均勻地打在窗上,望著雨水在玻璃上劃落的痕跡,蘇響開始想念一個在江西打游擊戰的人。蘇響的耳畔于是就響起了槍炮聲和地雷爆炸時沉悶的聲音。她想象著炸彈的沖擊波把泥石掀起來的場景,也想著一些同志穿越密林時的身影,同時她又望著密密的雨陣想,看樣子程大棟只是在她生命中突然下的一場陣雨。
陳淮安搖晃著身體,舉著杯子和很多人打招呼和喝酒。他的精神狀態很好,作為大律師有很多人賣力而熱情地和他打著招呼。那天其實蘇響是聽到陳曼麗麗和陳淮安的爭吵的,他們躲在一個暗處熱烈地吵著,仿佛一定要把一件事吵出一個結果來。隔著那些晃動的人頭,蘇響看到陳曼麗麗的臉上全是淚水。
陳曼麗麗口齒清晰地說,你爸王八蛋。
蘇響聽到這些的時候,她皺著眉瞇起了眼睛。但是最后她沒有對任何人說什么,她端著酒杯就像是皮影戲里一個飄渺的人物,飄蕩在那個歌舞升平的雨夜。
她只對自己說了一句話,一切為了勝利。
那個有著微雨的夜晚,蘇響陪著陳淮安走出金字塔房,去了沙遜大廈頂樓的露臺。陳淮安喝醉了,他站在潮濕的空氣里,對著蘇響大聲地說,你能不能嫁給我。蘇響一言不發,她想起了梅娘說的,組織上希望她能和陳淮安結婚。
陳淮安的一條腿跪了下來,跪在爛濕的沙遜大廈露臺上。雨顯然已經停了,他的臉上有了明顯的淚痕。陳淮安十分認真地說,蘇響,我要你嫁給我。蘇響走到了露臺邊,望著上海的夜色,她對著夜空說,你連鮮花也沒準備,你把我當什么?陳淮安隨即站起,他的臉上露出興奮的神色。陳淮安說:我送你一車的花。蘇響說,是我自己要出來的東西,我不會要。蘇響轉過頭,看到了陳淮安插在衣袋上的派克金筆。蘇響把那支筆拔了下來,擰開筆帽,在手底心上寫上了一個字:風。陳淮安說,什么意思?蘇響說,沒什么意思。你把這支筆給我吧,代替花。陳淮安說,那我給你買支新的。蘇響說,不要,就要這支。那天晚上陳淮安開車把蘇響送回西愛咸斯路73號。陳淮安的車子開走后,蘇響叫了一輛黃包車去了梅娘的家。她在梅娘家門口站了很久,四面八方的黑色的夜向她奔涌而來。在這樣的黑夜里,她有想哭的沖動。她十分想念程大棟,所以她最后還是哭了起來。她哭得酣暢淋漓,最后哭得蹲下身去。她說程大棟你為什么還不回來還不回來還不回來?這時候屋里的電燈光亮了,梅娘披著衣坐起身來,順手就點起了一支煙。
怎么了?梅娘的聲音從屋里傳了出來。蘇響止住哭,她對著玻璃窗上梅娘的剪影認真地說,我要嫁給陳淮安了。
米高梅舞廳的音樂聲里,金大班把陳曼麗麗領到陶大春面前。陶大春穿著合身的西裝,他今天的身份是販酒的商人。平常陶大春偶爾會喝一些酒,所以他對酒比較了解,即興地就把今天的身份定為酒販。金大班戴著白色滾絲邊的手套,叼著一支細長的香煙,拿一雙微微有些吊起來的丹鳳眼說,陶老板儂要好好之謝謝我。
陶大春似笑非笑,他的目光就一直落在陳曼麗麗的身上。陶大春說,我們又見面了。
陳曼麗麗在陶大春的大腿上坐了下來說,沒一個男人不這么說。
陶大春說,你要是不是舞小姐,你就像一名小學老師。你甚至像一名女校的校長。
陳曼麗麗捏了陶大春一把說,陶老板你抬舉我了。謝謝你那么多次關照我。
陶大春說,我真想娶你。
陳曼麗麗說,你不會!你只會逢場作戲。這話陳淮安以前也說過很多次,我和你說起過。
陶大春笑了,我還知道你恨死他那個王八蛋的爹了。
陶大春那天和陳曼麗麗跳了很久的舞,也喝了很久的酒,那天是陶大春比較放松的夜晚。軍統在上海的工作處處受挫,同時卻又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陶大春被自己的身份和工作迷惑了,他樂此不疲地把一條命拴在褲腰帶上,在血雨腥風的上海街頭滾打。這一次他來舞廳的真實意圖,是來和一個人接頭的。
陳曼麗麗挽著陶大春的手和陳淮安、蘇響碰到的時候,是他們一連跳了七支舞以后。他們跳完一曲走向座位,陳淮安和蘇響顯然才剛剛趕到舞廳,差一點還撞了滿懷。蘇響看到陶大春一身西裝,知道陶大春大概又是在執行什么任務。陳曼麗麗把頭昂了起來,這一次她像是對陳淮安示威般的,緊緊地挽住了陶大春的手。陶大春拍拍陳曼麗麗的手對陳淮安說,謝謝你以前對陳曼麗麗的關照。
四人相對,有些尷尬。陳淮安無法接陶大春的話,他不知道該怎么接。只有陶大春是從容的,他微笑著,根本就不像一個吳淞口碼頭貨場的記賬員,也不像是黃包車夫。他就像一個留連舞廳的歡場里的公子。
陶大春說,要不是你現在找的女人是我喜歡的女人,我一定出錢讓斧頭幫的馮二把你給卸了。陳淮安也笑了說,你就不怕法律的制裁嗎?在國家都沒有的時候,法律是個屁。你究竟想說什么?陶大春笑了,拍拍陳淮安的肩說,我只想說一句,你對蘇響必須得好一些。陶大春話還沒有說完,一個穿黑西裝的男人向陶大春走來,他一邊走一邊脫著禮帽。陶大春看到他的動作,知道他要找的接頭人來了。而此時從樓梯上奔下來五六名漢子,他們撞到了一張桌子,迅速地向陶大春和禮帽靠攏。陶大春和禮帽撒腿就跑,尖叫聲中舞場內隨即亂了起來。一名漢子手中揮起的刀迅速劈向了禮帽,一條胳膊隨即被卸了下來。那條帶血的胳膊死氣沉沉地就躺在蘇響、陳曼麗麗和陳淮安的腳邊,跳舞的男人女人和陳淮安一樣,都嚇得往后直退。在舞客們劇烈的如同潮水退潮一般的喧嘩聲中,蘇響和陳曼麗麗卻反應平靜。
蘇響說,你挽錯了男人的胳膊了。陳曼麗麗話中有話地說,我從來都沒有挽對過男人的胳膊。此刻從舞廳里追出來的五六名漢子站在舞廳門口,望著路上的行人、燈光與車輛,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他們手中都握了一把刀,愣愣地四下張望著。那時候一輛電車正響著叮叮的聲音,緩慢如蛇行般向這邊寂寞地駛來,而陶大春和禮帽顯然已經不見了蹤影。
蘇響不知道,此刻在二樓的包廂里坐著她同父異母的哥哥龔放。他穿著黑色的風衣,正在十分專注地品一壺普洱茶。他的懷里就抱著那個可愛的布娃娃,他甚至舉起布娃娃親了一下。剛才他站在二樓護欄邊讓五六名特工奔下樓的時候,已經看到了妹妹蘇響挽著陳淮安的手站在舞廳里。他果斷地揮了一下手后,就又走進了包廂喝茶。
一會兒一名漢子匆匆進來,垂手站在龔放的面前說,隊長,人跑了,砍下一只手來。
龔放喝了一口普洱茶,抬起頭來用陌生的目光望著這名漢子:手有什么用?又不是火腿!
龔放說完又埋下頭去喝茶,他吸了吸鼻子,仿佛是要吸凈普洱的香味。當漢子們陸續回到了包廂的時候,龔放平靜地說,一群廢物。
龔放又聞了聞茶水,喝了一口說,好茶。
蘇響拿著喜帖坐在龔放辦公室的沙發上。看上去龔放白凈的臉上沒有血色,在昏暗的屋子里,龔放一步步踱過來,拿起喜帖認真地看了一眼說,你長大了。
蘇響說,人總是要長大的。
龔放說,可惜我長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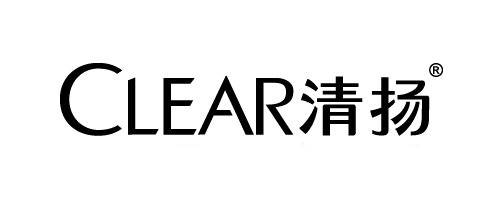

 粵公網安備44030702000122號
粵公網安備4403070200012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