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大家都退出之后,他才起身走向梅長蘇,道:“看你的意思,似乎對于將帥的人選,已經有了大概的想法?”
“是。”
“別跟我說你要去。
就是我去也不會讓你去地。”
“那我們就先說說別的,”梅長蘇也沒強爭,“這場戰事必須動用赤焰舊將。
這一點殿下沒有異議吧?不是我自夸,雖然帶的不是熟悉地兵。
但赤焰人的聲名擺在哪里,首先就不需要擔心屬下兵將是否心服地問題。”“這是當然。
對赤焰舊將而言,立威這個過程并不難,大家心里都是敬服的。”蕭景琰贊同道,“再說沉冤方雪就臨危受命。
只會令人感佩。
若派了其他人去,怕只怕將士們的“誰?”
“蒙摯。”
蕭景琰眉頭一皺,立時就要反對,被梅長蘇抬起一只手制止住了,“蒙大哥以前在軍中時,就以作戰勇猛著稱,頗有幾件傳奇軼事,名聲很高,他又是我們大梁的“我聽衛崢說,你有一個蒙古大夫吧?”沉思半晌后,蕭景琰想到了一個拒絕的借口,“我要見見他,如果他說你可以去,我就同意……”
聽到這個要求,梅長蘇的眸中突然快速閃過了一抹復雜的神情,不過瞬間之后就消失了,再仔細看時,表情已被控制得相當完美。
“好吧,我回去跟藺晨說說。”梅長蘇微微欠身,“籌措出征,殿下還有一大堆事要辦,我先告退了。”
蕭景琰被他自若的神態弄得心里略略發慌,總覺得有些什么掌控之外的事情在肆無忌憚地蔓延,可細細察時,卻又茫然無痕。
不過這股異樣的情緒并沒有持續多久,因為前方急報很快又一波接一波地涌了進來,瞬間便占據了他的全部思緒。
一系列的兵力調動、人事任免、銀糧籌措、戰略整合,各部大臣們輪番的議稟奏報,忙得這位監國太子幾乎腳不沾地,甚至沒有注意到梅長蘇是什么時候悄悄退出的。
比起緊張忙碌的東宮,蘇宅顯得要安靜寧和得多。
不過戰爭的陰霾已經彌漫了整個京師,蘇宅也不可能例外,當梅長蘇進門落轎之后,大家雖極力平抑著,但投向他的目光還是不免有些躁動不安。
“請藺公子來。”梅長蘇簡略地吩咐黎綱后,徑直便回到了自己的臥房。
片刻后,藺晨獨自一人進來,臉上仍是帶著笑,站在屋子中央,等著梅長蘇跟他說話。
可是等了好一陣子,梅長蘇卻一直在出神,他只好自己先開口道:“我剛剛出去了一趟,你有幾個小朋友正在募兵處報名從軍呢。
看來這世家子弟也分兩種,一種如同蠕蟲般醉生夢死毫無用處,另一種若加以磨礪,卻可以比普通人更容易成為國之中堅……”
“國難當頭,豈有男兒不從軍的?”梅長蘇語調平靜地道。
“藺晨,我也要去。”
“去哪里?”
“戰場。”
“別開玩笑了,”藺晨的臉色冷了下來。
“現在已經是冬天,戰場在北方,你勉強要去。
又能撐幾天?”三個月。”
他答的如此快捷,令藺晨不禁眉睫一跳。
唇色略略有些轉白。
“聶鐸帶來了兩株冰續草,”梅長蘇的目光寧和地落在他地臉上,低聲道,“此草不能久存,你一定已經將它制成了冰續丹。
是吧?”
“你怎么知道的。”
“這里是蘇宅,我知道有什么奇怪?”
藺晨背轉身去,深吸了兩口氣道:“你知道也沒用,我不會給你的。”
“你地心情,我很明白。”梅長蘇凝望著他的背影,靜靜地道,“如果按原計劃,我們一起去賞游山水,舒散心胸。
那么以你地醫術,也許我還可以再悠悠閑閑地拖上半年……一年……或者更久……”
“不是也許,是可以。
我知道自己可以!”藺晨霍然回頭,眸色激烈。
“長蘇。
舊案已經昭雪,你加給自己的重擔已經可以卸下。
這時候多考慮一下你自己不過分吧?世上有這么多的事,一樁樁一件件永不停息,根本不是你一個人能解決完的!你為什么總是在最不該放棄的時候放棄?”
“這不是放棄,而是選擇,”梅長蘇直視著他地雙眼,容色雪白,唇邊卻帶著笑意,“人總是貪心的,以前只要能洗雪舊案,還亡者清名,我就會滿足,可是現在,我卻想做的更多,我想要復返戰場,再次回到北境,我想要在最后的時間里,盡可能地復活赤焰軍的靈魂。
藺晨,當了整整十三年的梅長蘇,卻能在最后選擇林殊的結局,這于我而言,難道不是幸事?”
“誰認識林殊?”藺晨閉了閉眼睛,以此平息自己的情緒,“我萬辛萬苦想讓他活下去的那個朋友,不是林殊……你自己也曾經說過,林殊早就死了,為了讓一個死人復活三個月,你要終結掉自己嗎?”
“林殊雖死,屬于林殊地責任不能死。
但有一絲林氏風骨存世,便不容大梁北境有失,不容江山殘破,百姓流離。
藺晨,很對不起,我答應了你,卻又要食言……可我真的需要這三個月。
就公義而言,北境烽火正熾,朝中無將可派,我身為林氏后人,豈能坐視不理,茍延性命于山水之間?從私心來講,雖然有你,但我終究已是去日無多,如能重披戰甲,再馳沙場,也算此生了無遺憾,所得之處,只怕遠遠勝過了所失……”梅長蘇用火熱的手掌,緊緊握住了藺晨地手臂,雙眸燦亮如星,“冰續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奇藥,上天讓聶鐸找到它,便是許我這最后三個月,可以暫離病體,重溫往日豪情。
藺晨,我們不言大義,不說家國百姓,單就我這點心愿,也請你成全。”
藺晨怔怔地看著他,輕聲問道:“那三個月以后呢?”
“整個戰局我已經仔細推演過了,敵軍將領地情況我也有所掌握,三個月之內,我一定能平此狼煙,重筑北境防線。
對于軍方地整飭,景琰本就已經開始籌劃,此戰之后,我相信大梁的戰力會漸漸恢復到鼎盛時期。”
“我是說你,”藺晨眸色深深,面容十分沉郁,“三個月以后,你呢?這冰續丹一服下去,雖然能以藥效激發體力,卻也是毫無挽回余地地絕命毒藥,三月之期一到,就是大羅神仙,也難多留你一日。”
“我知道。”梅長蘇淡淡地點頭,“人生在世,終究一死。
藺晨,我已經準備好了。”
藺晨牙根緊咬,一把扯開自己的衣襟,從內袋處抓出一個小瓶,動作十分粗暴地丟給了梅長蘇,冷冷道:“放棄也罷,選擇也好,都是你自己的決定,我沒什么資格否決,隨便你……”說著轉身,一腳踹開房門,大步向外就走。
“你去哪里?”
“外頭的募兵處大概還沒關吧,我去報名,”藺晨只是略停了停腳步,頭也不回地道,“我答應過要陪你到最后一日。
你雖食言,我卻不能失信,等有了軍職。
請梅大人召我去當個親兵吧。”
梅長蘇心頭一熱,冰涼的小瓶握在手中。
突然開始發燙。
守在院子里的其他人雖然不知道冰續丹的存在,也不知道兩人談話地細節,但從藺晨走時所說的這句話,大約也能推測出梅長蘇已經決定出征北境。
幾個侍衛都是熱血小伙,黎綱和甄平更是舊時軍士。
他們一方面都想要上疆場衛國殺敵,另一方面又怕梅長蘇經受不起征戰艱苦,矛盾重重之下,都呆呆地站在院中,不知該作何反應才好。
在一片僵硬的氣氛中,宮羽抱琴而出,廊下獨撫。
纖指撥捻之間,洗盡柔婉,鏗鏘錚錚。
一派少年意氣,金戈鐵馬,琴音烈烈至最高潮時。
突有人拍欄而歌:“想那日束發從軍,想那日霜角轅門。
想那日挾劍驚風。
想那日橫槊凌云……流光一瞬,離愁一身。
望云山,當時壁壘,蔓草斜曛……”
歌聲中,梅長蘇起身推窗,注目天宇,眉間戰意豪情,已如利劍之鋒,爍爍激蕩。
越一日,內閣頒旨,令聶鋒率軍七萬,迎戰北燕鐵騎,蒙摯率軍十萬,抗擊大渝雄兵,擇日誓師受印。
在同一道旨意中,那位在帝都赫赫有名地白衣客卿梅長蘇,也被破格任命為持符監軍,手握太子玉牌,隨蒙摯出征。
臨出兵的前一天,梁帝大概是被近來地危局所驚,突發中風,癱瘓在床,四肢皆難舉起,口不能言。
蕭景琰率宗室重臣及援軍將領們榻前請安,并告以出征之事。
當眾人逐一近前行禮時,梅長蘇突然俯在梁帝的耳邊,不知說了些什么,早已全身癱麻的老皇竟然立時睜大了眼睛,口角流涎,費力地向他抬起一只手來。
“父皇放心,蘇先生是國士之才,不僅通曉朝政謀斷,更擅征戰殺伐。
此次有蒙卿與他,亂勢可定,從此我大梁北境,自可重得安固。”站在一旁的蕭景琰字字清晰地說著,眸中似有凜冽之氣。
梁帝的手終于頹然落下,歪斜地嘴唇顫抖著,發出嗚嗚之聲。
曾經的無上威權,如今只剩下虛泛的禮節,當親貴重臣們緊隨著蕭景琰離開之后,他也只聽得見自己粗重的呼吸聲,在這幽寒冷硬、不再被人關注的深宮中回蕩。
第二天,兩路援兵的高級將領們便拜別了帝闕,束甲出征。
如同當年默默看著梅長蘇入京時一樣,金陵帝都的巍峨城門,此刻也默默地看著他離去。
到來時素顏白衣,機詭滿腹,離去時遙望狼煙,躍馬揚鞭。
兩年的翻云覆雨,似已換了江山,唯一不變的是一顆赤子之心,永生不死。
初冬地風吹過梅長蘇烏黑的鬃角,將他身后的玉色披風卷得烈烈作響。
烏騅駿馬,銀衣薄甲,胸中暢快淋漓地感覺還是那么熟悉,如同印在骨髓中一般,拔之不去。
放眼十萬男兒,奔騰如虎,環顧愛將摯友,傾心相持。
當年梅嶺寒雪中所失去的那個世界,似乎又隱隱回到了面前。
煙塵滾滾中,梅長蘇地唇邊露出了一抹飛揚明亮地笑容,不再回眸帝京,而是撥轉馬頭,催動已是四蹄如飛的坐騎,毅然決然地奔向了他所選擇地未來,也是他所選擇的結局。
尾聲大梁元佑六年冬末,北燕三戰不利,退回本國,大渝折兵六萬,上表納幣請和,失守各州光復,赦令安撫百姓。
蒙摯所部與尚陽軍敗部合并,重新整編,改名為長林軍,駐守北境防線。
在這次戰事中,許多年輕的軍官脫穎而出,成為可以大力栽培的后備人才。
蕭景琰、言豫津也皆獲軍功,只是前者因身世之故,辭賞未受。
對于百姓、朝臣和皇室而言,這是一場完整的勝局,強虜已退,邊防穩固,朝堂上政務軍務的改良快速推進著,各州府曾被摧毀的家園也在慢慢重建。
大多數歡欣鼓舞的人們在一片慶賀的氣氛中,似乎已經忽略了那些應該哀悼的損失。
但蕭景琰沒有忘記,他在東宮的一間素室中夙夜不眠地抄寫本次戰事中那些亡者的名字,從最低階的士兵開始抄起,筆筆認真。
可是每每寫到最后一個名字時,他卻總會丟下筆伏案大哭,悲慟難以自抑,連已懷有身孕的太子妃,都無法從旁勸止。
元佑七年夏,聶鐸從東海歸來述職。
但他與霓凰的婚事,蕭景琰總是不肯答應,直到有一天,宮羽帶來了梅長蘇所寫的一封信,他才默默首肯。
婚后霓凰將南境軍交給了已日趨成熟的穆青,隨同聶鐸叩別林氏宗祠,一起去了東境駐守海防。
元佑七年秋,太子妃產下一名男嬰。
三日后,梁帝駕崩。
守滿一月孝期,蕭景琰正式登基,奉生母靜貴妃為太后,立太子妃柳氏為皇后。
庭生果然被蕭景琰收為義子,指派名師宿儒,悉心教導。
由于他生性聰穎,性情剛強中不失乖巧,蕭景琰對他十分寵愛,故而他雖無親王之份,卻也時常可以出入宮禁,去向太后和皇后請安。
長壽的高湛依然掛著六宮都總管的頭銜,只是現在太后已恩準他養老,可以在宮中自在度日,不須再受人使役。
高湛十分喜歡那個玉雪可愛的小皇子,常去皇后宮中看他,每次庭生抱小皇子在室外玩耍時,他都要堅持守在旁邊。
“高公公,你要不要抱抱他?”看著這滿頭白發的老者眼巴巴在旁邊守護的樣子,庭生有時會這樣笑著問他,但每次高湛都躬著身子搖頭,顫巍巍地說:“這是天下將來的主子,老奴不敢抱……”
對于他的回答,庭生似乎只當清風過耳,并不在意,仍舊滿面歡笑地,引逗著小皇子呀呀學語。
“看他們兄弟倆,感情可真是好,”旁邊的奶娘一邊笑微微地說著,一邊注意天色,“不過也該抱進去了。
天這么陰,高公公,你覺不覺得……好象起風了?”
“不,不是起風了,而是在這宮墻之內……風從來就沒停過……”瞇著昏花的雙眼,歷事三朝的老太監如是說。
(完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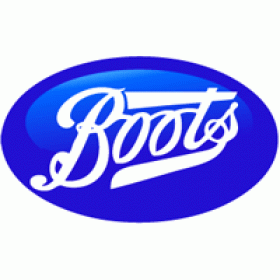




 粵公網安備44030702000122號
粵公網安備44030702000122號